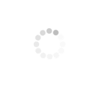
他体会过自由,明白善的意义
——————————————
——于坚文化心态略论
文|朵渔
前言
这篇文字是八年前应《诗建设》杂志所约而作,如今读来,有些说法已不尽适当。但感觉对“保守主义”的阐发尚有可读之处,因此重新贴出。
前年秋天,老于从西方云游归来,在我家中小住。酒酣耳热之际,我们曾争论过一个话题:就现实问题,我提倡“直接说”,他表示很担心。我的意思是,该说的你就说嘛,这是你的权利,绕那么多圈子干什么?我为此写过一篇小文:《无尽的反讽是一种消磨》。在目前的社会情态下,我们似乎与黑暗中的捕手达成了一项契约:你知我知,大家心知肚明,就是不能说透。它隐含的意思是,你可以这么认为,但你不能明说,如果你直接说出了,你就犯规了,就要承受代价。如果彼此双方接受了这项契约,那就意味着我们是在一种不自由的情态下创作的,我们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并接受了一个犬儒的命运。
诗人要不要就现实说话,从来都是鸡鸭争鸣,纠缠不清。我们暂且站在鸡这一边——对于那些赞成“介入现实”的诗人而言,到底该如何说话。事实上,即便那些口口声声“诗歌与现实无关”论者,如果你批评他们“犬儒”,他们也觉得很委屈。北岛曾隔海狠批大陆诗人“犬儒化”,有些诗人就表现得很委屈,认为自己该说的都说了。问题是,你说什么啦?一句话绕八道弯,到底是想让人明白还是想让人糊涂?你那点优雅的转体、带唾沫味儿的俏皮话真的很高明吗?赫塔·米勒有些愤慨地指出,在独裁统治下,欣赏俏皮的、几乎天衣无缝的幽默,也意味着美化它的离题。“无望中诞生的幽默,绝望之处生出的噱头,模糊了娱乐与羞耻之间的界限。幽默需要出人意料的高潮,只有不留情面才会引人入胜,绽放言语的光芒。” (《每一句话都坐着别的眼睛》) 事实上,没有人真的就认为诗歌是一种对现实政治的直接干预,诗歌阻挡不了坦克,这是一种你被迫接受的常识。但在被金钱和权力牢牢控制的世界一体化面前,在体制矛盾日益加深的日常世界里,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将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希望,这正是我们所期颐的诗歌伦理。在表层意义上,诚如萨特所言:尽管文学是文学,道德是道德,在美学必需的深处,我们也感到了道德的必需。如果你感受不到也没关系,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诗歌本身就带有政治性,它反对的是“全球化的强制普遍性,金钱和权力的强制普遍性”,它是“人的解放的一部分”。 (阿兰·巴丢语)
老于向来“拒绝隐喻”,事实上他差不多是在“直接说”了,无论是诗之内还是诗之外。但他不乐于承认。我有时觉得,他的担心只是出于一种生理本能,那是历史阴影和人生阅历埋在他体内的一根引线。在诗歌之外自不必说,他在很多场合都在以“诗人”的身份发言,并试图把诗歌重新纳入公共话语的范畴。在诗之内,他的言说方式也近乎杜甫的“三吏三别”。读他近几年的作品,很多“歌行体”,涉及环保、拆迁、日常暴政等等,近乎小型诗史。他保持了他一贯的“浅白”风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滔滔不绝。这种风格也为他带来很多风议——当一个诗人一览无遗地坦白自己时,他的读者总是在智力上不买账。尼采曾讲过两类作家:才思敏捷的作家的不幸在于人们认为他们很肤浅,因为读他们的作品不必花费什么力气;而思路不清晰的作家的运气则在于读者费尽心力读他们的书,并将他自己努力中的乐趣归于他们。所谓“写得清楚的拥有读者,写的模糊的拥有评论家”,这是双重的误会。老于的作品有亲和力,风格近乎浅白,但“浅白”绝非肤浅,事实上他有其清晰的文化立场和深意寄焉。而那些风格晦涩的诗人,其实也易于招人嫉恨,因为他们总是显得高高在上,不仅在姿态上、更是在智力上羞辱他的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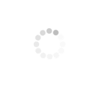
诗人的晦涩风格仅仅是一种个人趣味,还是有其诗学本源?本雅明在《论趣味》一文中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他说手艺人在面对买主的时候,总是希望买主对产品一无所知,因为这样更有利可图。如何诱惑和蒙骗买主?最好是加强商品表面的繁复程度,让其沐浴在一层“神秘之光”里。随着顾客专门知识的衰退,趣味的重要性就更加重要。“对于顾客来说,趣味以一种繁复的方式掩盖了他自己缺乏行家眼光的事实,而对厂家来说,趣味给消费带来新鲜的刺激,给消费者带来满足感,从而消除了他的其他要求。”文学上的“为艺术而艺术”反映出来的正是这种变化。“为艺术而艺术”者其实并没有什么急切的东西想要表达,他最多也就是想把自己带入语言,“包括他自己的小怪癖、小精妙,和他天性上那些根本称不出份量的东西”。当一个诗人从一切具体的经验里抽身出来,他也就只能在一些词语中挑挑拣拣,制造表面的、繁复的、所谓的“语言炼金术”。“要把生产活动建立在这种退场的基础上,就会遇到具体的、难以逾越的困难。正是这些困难将马拉美的诗变成了神秘晦涩的诗。”
事实上不仅是风格晦涩的诗,包括很多披着理论外衣的口水诗、复古诗、神性诗,都是一种建基于“趣味”基础之上的空心诗。老于反对这种空心化,他总是有话要说。当他开口说话,他的文化立场就近乎于保守主义。保守和守旧不同。守旧是认为有“旧”可守,存在着一个可资缅怀的“黄金时代”。保守主义的对立面是激进主义,激进者常认为生活在别处,“黄金在天上舞蹈”。保守主义者则认为,从来就没有黄金时代,过去不曾有,未来也不会有。因此保守主义者强调经验、强调常识,强调具体特定的事情,对抽象的、先验的原则充满质疑。保守主义在哲学上具有浓厚的怀疑主义色彩。他们在“进步”面前会非常审慎,不喜欢“干大事”,“做大做强”,也轻易不会干出类似“断裂”那样的事情。他们宁愿把自己的思想建立在经验和现实之上,相信秩序、正义和自由是漫长而痛苦的社会经验的产物。尽可能避免对它进行釜底抽薪的改造。因此他们天生不是革命者。革命者往往建基于飞扬的浪漫主义之上,“浪漫主义,那是革命。革命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呢?显然是一切。”保守主义则是一定程度的传统主义加上古典自由主义的融合,而且随着时代之变迁以及保守内容的不同,保守主义者总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在春天和夏天是改革者,在秋天和冬天却成了守旧派。我们在早晨是改革者,在夜晚是保守者。” (爱默生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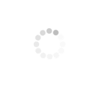
全球化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困境是,我们被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牢牢控制着,“金钱的普遍性,信息的普遍性和权力的普遍性。这就是今天的普遍性”。 (巴丢语) 艺术如何靠自己的创造来打破这种普遍性?巴丢说:“我的立场是,今天的艺术创造应该提出一种新的普遍性,不仅表达社群的本性,而且,艺术创造有必要为我们,为共有的人的状况,提供某种新的普遍性,我把它称之为真理。” 巴丢所言的艺术真理,是一种知觉或感性的真理,是“知觉转化成了理念的一个事件”,是“关于在世的感性经验的一项主张”。艺术正是靠这种新的创造,来对抗全球化所带来的抽象普遍性。在此意义上,艺术是人的解放的一部分。尼采为欧洲人的幻灭感开出的药方是,把艺术作为人所固有的形而上活动,即通过艺术赋予本无意义的世界和人生以一种形而上的意义。尼采的艺术学不是美学而是生命学,在面对世界信仰的破产时,我们还能够设法将我们的人生骄傲地看作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就像看待一件自创的艺术品一样看待人生,只有这样,生存对我们来说才是可承受的。换一种说法,面对永恒循环的生命,人通过艺术创造而具有了双重身份:人既是大自然的艺术品,又是艺术家;既是被造之物,又是创造者;既渺小,又伟大。面对空虚无聊、缺乏深度、处于“拔根”状态的时代精神状况,尼采呼吁欧洲向古代希腊人学习,去那里寻找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本源性的东西,以此来对抗弥漫欧洲的虚无主义。
老于是贴着“先锋”的标签被主流诗坛接受的。直到世纪末,一个早已熟透的中年诗人还被称作“青年先锋诗人”,这让人情何以堪。我们这里缺少一种老年诗人的典型形象,多的是早夭的才子,激烈的反叛者和先锋派,却没有一个清明澄澈、老而弥坚、“老来诗篇浑漫与”的老年诗人形象。真正伟大的诗人,是可以贯穿一生的。当现代汉语诗歌有了它的老年形象,才算有了一个完整的传统。一个诗人,要像杜甫那样完成自己一生的形象,是很难的。章太炎曾说,李翱后来师事药山,韩愈后来师事大癫,都是晚年落魄意气颓唐之举。很多诗人,一过中年,便无足观,大概也是在精神上没有挺住吧。老于的“中年变法”,既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是人生历练的自然反应。人过中年,已将人生的巨石推到山顶,幻灭感和焦虑感便会油然而生。这个时刻,挺住的确意味着一切。稍有颓唐,人生的巨石便会滚下山去。艺术作为一种自救的良药,其疗效完全在于甘苦自知,挺不住的概率极高。新世纪以来,老于开始有意识地亲近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并声称“先锋也可以是后退”。后退,就是要摒弃弥漫于二十世纪的革命思维,回到常识和中道上来。轻言传统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的时代,传统往往意味着一双民族主义的小脚。老于有一种“气吞山河”的气势,他试图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吞到胃里强行消化。这很容易导致一种风格上的消化不良症,满嘴的腐臭真比青春痘还让人难堪。看看那些浑身雕饰着传统意象的嗜古患者,就不难明白。章太炎曾论韩柳:韩才气大,我们没见他的雕琢气;柳才气小,就不能掩饰。老于的确有很强的消化能力,愣是六经注我,别开生面。加之他多变的题材和风格,这条路让他走活了。
老于推崇常识和经验,贬斥抽象的口号。“别说得那么抽象吧/永恒具体得很/不必去瞻仰浩瀚星空/就数数脚下的沙子/捧一把置于掌心叹口气 /沾些口水 一粒接着一粒请点数 哲人” (《便条集:在沙漠与绿洲之间 6》) 。对日常生活世界的亲近,与自然和家国情怀的融合,使他保持了很好的常识感。他是他那一代诗人里尚未泯灭纯洁之心的少有的诗人之一。在知识来源上,老于有一种重返古典轴心的雄心。他热爱古代文化,尤其是作为源头活水的诸子群经。最近些年来,“为天地立心”越发成为他念兹在兹的文化理念。这使他的诗歌经验越发驳杂起来。他有时会动用日常生活的经验,观察日常世界:“妈妈老啦/这一辈子她织过无数毛衣/有些合我的身段/有些被异乡人穿走” (《妈妈老啦》) ;有时又会用一种旷古的眼光来打量世界:“他来自傲慢的大陆/五千年的历史足以令他在掏出护照时/慢条斯理庇护者河流纵横/高原上埋着陶罐 有些花纹的含义至今未破/落日下的平原也是金黄的/巴比松画派从未调出过这种色” (《入境遭遇》) ;有时他在低处,从大海里捞盐;有时又在高原:“高于大地领导亚细亚之灰/披着袍 苍茫的国王站在西双版纳和老挝边缘” (《大象》) 。老于是将几种视角有效地综合在自己身上,让他的诗作变得不古不俗,不偏不狭。如果一个诗人仅用一种视角来写诗,很容易陷入自我的窠臼里出不来,在自我营造的风格里孤芳自赏,不再接纳异质的东西。一旦如此,他也就固步自封,难以为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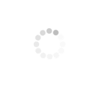
新时期以来,汉语诗歌基本上是一种亦步亦趋的学步状态,好像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这种“进步”心态就是“没有最新,只有更新”,不是最新的,肯定就不是最好的或最高级的。所谓“新诗—现代诗—当代诗”的阶梯式划分,大概就是这么来的。求新求变带来的副作用大概就是立足不稳,空心化,游戏化。写作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面对“被先锋耗尽的诗歌”,老于采取的策略是:不跟了。他的“后退”姿态大概就是这么来的。他想去求取那种最根本的东西——“道”,并试图在日常世界中“道成肉身”。这个“道”,与历次“文艺复兴”冲动所求取的那个东西差不多,并未偏离我们传统的“道统”。表现在风格上,虽有别于传统诗教的“温柔敦厚”,但也接近于“中道”。广大,中正,不偏不倚。“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求其正声,这大概就是老于的理想境界吧。
从个人性情上说,老于其实是三分杜,七分李。他诗歌中飞扬的部分——也就是浪漫主义的东西更多一些。他虽自称“像俗人一样生活”,却要求“像上帝一样思考”;他明知“识时务者为俊杰”,却经常“仰天大笑出门去”;他可以写到尘埃里,但调子永远起得很高;他时常会在一些很具体的事物上入神,却又会在世俗生活中神不守舍。他一方面强调汉语诗歌的“汉语性”,试图保持一种客观、清明、冷静的风格,一方面又对那种原始的、神秘的、粗野的东西充满好奇。保守主义者往往对浪漫主义——无论是革命浪漫主义还是青春浪漫主义——都无好感,而且充满芥蒂。在某种程度上,飞扬的浪漫主义就是对“中道”的偏离。如果严守“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诗教,对浪漫主义的排斥是很自然的。强调秩序、自我克制和纪律的老歌德就从未对浪漫主义施以援手,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说:“浪漫主义是病态的,古典主义是健康的。”即便如此,歌德依然被视为浪漫主义的父执,因为他的《威廉·迈斯特》。老于也在将他性情中的浪漫主义和他文化心态上的古典主义做一种有效的中和。事实上,保守主义与浪漫主义并无矛盾。保守主义者保守那些传统中普世的、恒久的、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个人自由;浪漫主义的最终结局也是自由主义,是宽容,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于不完美生活的体谅,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强。在此意义上,二者又殊途同归于自由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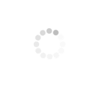
现在谈起浪漫主义来,总让人心怀疑虑,因为我们经历过一个不太成功的才子佳人般的浪漫主义幼稚期,以及被意识形态吞噬掉的革命浪漫主义时期。加之我们还有一个“诗歌进步”观,很多诗人都讳言“浪漫主义”,似乎一浪漫主义就将自己十九世纪化了。这是对浪漫主义的误解。以赛亚·伯林曾以其令人销魂的咏叹调般的才思,为浪漫主义下过一个定义:
浪漫主义是原始的、粗野的,它是青春,是自然的人对于生活丰富的感知,但它也是病弱苍白的,是热病、是疾病、是堕落,是世纪病,是美丽的无情女子,是死亡之舞,其实就是死亡本身。是雪莱描绘的彩色玻璃的圆屋顶,也是他永恒的白色光芒,是生活斑斓的丰富,是生活的丰盈,是不可穷尽的多样性,是骚动、暴力、冲突、混沌;它又是安详,是大写的“我是”的合一,是自然秩序的和谐一致,是天穹的音乐,是融入永恒的无所不包的精神。它是陌生的、异国情调的、奇异的、神秘的、超自然的;是废墟,是月光,是中世纪的城堡,是狩猎的号角,是精灵,是巨人,是狮身鹫首的怪兽,是飞瀑,是弗洛斯河上古老的磨坊,是黑暗和黑暗的力量,是幽灵,是吸血鬼,是不可名状的恐惧,是非理性,是不可言说的东西。它又是令人感到亲切的,是对自己的独特传统一种熟悉的感觉,是对日常生活中愉快事物的欢悦,是习以为常的视景,是知足的、单纯的、乡村民歌的声景——是面带玫瑰红晕的田野之子的健康快乐的智慧。……它是极端的自然神秘主义,也是反自然主义的极端唯美主义;它是能量、力量、意志、青春,是自我的展现,它也是自虐、自残、自杀;它是原始的、单纯的,是自然的胸怀,是绿色的田野,是母牛的颈铃,是涓涓小溪,是无垠蓝天。然而,它也是花花公子,是打扮的欲望。……简言之,浪漫主义是统一性和多样性。它是美,也是丑;它是为艺术而艺术,也是拯救社会的工具;它是有力的,也是软弱的;它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它是纯洁也是堕落,是革命也是反动,是和平也是战争,是对生命的爱也是对死亡的爱。
(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
西方浪漫主义的兴起,是对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反动。一般人心目中,十八世纪是一个和谐、典雅、强调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口号是:“我们正在进步,我们正在发现,我们正在摧毁古老的偏见、迷信、无知和残忍,我们正在建立某种科学,以使人们生活得幸福、自由、道德和正义。”这和我们当下何其相似。而浪漫主义者则认为,世界是神秘的,搞不定的。浪漫主义最初的父执约翰·乔治·哈曼认为,上帝不是几何学家,不是数学家,而是诗人。除了理性,人类还具有非理性的因素,存在着潜意识的深层,内心涌动着各种黑暗的力量。艺术家的职责就是将这些黑暗的、无意识的东西挖掘出来 (谢林的观点) 。创作就是一种知性的冒险,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都是“非吾所知”的。凭借这种“非吾所知”的力量,艺术家才得以创造出深邃、广大的杰作。这样的艺术家近似于伟大的罪犯 (狄德罗的观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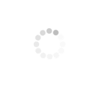
阿兰·巴丢在他的《当代艺术的十五个论题:怎样不做一个浪漫主义者?》一文中提出,“我认为,当代艺术的重大问题是怎样才能避免做一个浪漫主义者”。他这里所言的“浪漫主义”,其实是形式主义的浪漫主义。所谓“形式主义的浪漫主义”,就是把浪漫主义和形式主义混杂在一起,总是对新形式充满无限渴望,这事实上是对现代性的一个批判:总是求新求变,迷恋于形式的新奇。巴丢为此开出的药方是“做减法”。首先是从对形式的迷恋中后退,转而渴望某种稳定的东西,也就是对永恒的渴望。减法的第二个意思是不要迷恋有限性,不要迷恋身体、性、暴力、死亡等等黑暗的东西,因为艺术的最终命题是生的问题,而非死的问题。但他同时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必须正视人性中那非人性的一部分,因为非人性是人性中具有创造性的那一部分。“我们必须为存在于自身之外的这种人性,为这种可怕而丰饶的非人性的因素,发明一种象征性的再现方式。我把这样的再现称为一个英雄人像。”依靠这种“英雄主义”的东西,我们的人性才能彻底清晰地呈现出来。
我们都曾经中过浪漫主义的毒。但是,眼下到处充斥着被现实拖累得气喘吁吁的叙事诗,晦涩冷漠的技术流,以及苍白无力的反讽和段子。针对这种现状,我觉得是到了重提浪漫主义的时候了。因为浪漫主义并非仅属于一个时代,它是深潜于人类心灵的东西,是激情和想象力的最高体现。当外在暴力和自身的疲软交相侵蚀时,正需要唤醒/重塑这种内在的激情与之对抗。只有这样的对抗,才堪称有尊严的对抗,才堪称个人的胜利。
2012.2
书籍推荐
汉诗界 · 小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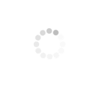
滑动查看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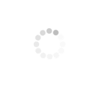
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购买书籍
或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微店选购更多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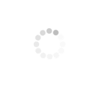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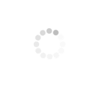
- E N D -
图片来源:于坚摄影作品
追蝴蝶 朵渔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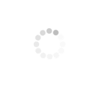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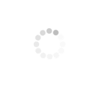
诗歌 | 艺术 | 思想
联系邮箱:69354885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