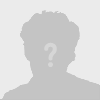讲师简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李白学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会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各类学术著作4部,先后荣获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奖励5项,主持、参与的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4项。
内容简介: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其中还不断出现另外一个人,苏轼。在反对变法的阵营中,苏轼算不上是重量级的人物,但天才纵横的他却是一个最活跃的人物,这给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制造了不少麻烦,也让皇帝宋神宗对他又爱又恨。然而,王安石和苏轼这对政治上的冤家却又是文学上的知音,比肩的道德与才华让他们相互欣赏和尊重,并由此生发出许多动人的故事,那么王安石和苏轼之间亦敌亦友的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呢?他们后来为什么能够冰释前嫌,而最初苏轼又是怎样反对王安石的呢?
全文:
神宗总是把苏轼有时候放在火上烤一烤,但不能把他烤焦了,烤焦了就麻烦了,烤上一阵子,觉得烤得发黄了,有点味道了,把他再拿下来冷却一下,还能用,烧焦了就没法用了,所以苏轼在这个、如果我们通观全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变法当中、在反对派当中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少的声音,但就是这样一个声音对于王安石来讲已经是相当烦恼了。再说还不是苏轼一个人在战斗,哥俩儿呢,苏轼和苏辙都是非常坚定地反对王安石所主导的变法。
苏轼和苏辙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反对变法的人,相反他们也有自己的变法和改革的主张,只不过对于苏轼来讲,他主张更加稳健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能是改良,特别在用人的问题上、在道德的问题上,他看得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说当改革一旦开始之后,苏轼和苏辙很快地就针对王安石的变法谈自己的反对的意见。
譬如说,王安石改革变法里边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科举的改革,科举有什么改革的呢?唐宋时期科举习惯的考核的内容,进士科主要是考诗赋,写诗写得好,苏轼就是自己在这方面考核是一个受益者,他的爸爸苏洵老是考不中,就是因为不善于有韵之文,他不善于写这种东西。王安石认为,以诗赋来取士,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因为什么呢,因为会写诗、会写漂亮的文章不等于说就有很深厚的学问和修养,不等于说就会执政、就会参政、就会做官,而改革变法需要的是这样的人,第一,他有很深厚的道德学养,第二,他有很强的实际的工作能力。只会写漂亮的诗文,只会写漂亮的诗赋这是不行的,所以,他要什么呢?废除诗赋取士的制度,考儒家的经典,考策论。物价涨得这么厉害,怎么解决啊?写篇策论吧。房价涨成这个样子,写篇策论,你怎么解决?你说先来首诗吧,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这没用,西湖边上的房子(房价)涨得很快,这玩意儿写得越多房价涨得越高。所以你知道吗?他改革科举不是他对诗赋本身有什么意见,而是着眼于实用。
他这个主张一出来,苏轼就坚决反对,苏轼给神宗就写了一道奏折,在这个奏折里边他重点说什么呢?说从古至今,他说的从古至今实际上就是从唐朝以来,一直都是诗赋取士,没有改变,而且天下的才子们和这些士子们,他们的发展方向就是跟朝廷规定的方向是要保持一致的。简单来说,他举了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比方说,就从写文章来说,如果说策论还算有点用的话,那诗赋是一点用都没有,策论还谈点实务嘛,你如果说从实际执政来讲,那诗赋跟策论都是扯淡了,没用,写那么多有什么用啊,就是干实事嘛。他说从尧舜以来,文人都是要写文章的,文人都是要写诗赋的,我们就是要根据写文章、写诗赋来判断一个人的才华,你总不能还没考试呢,就把一个人先弄去做上两天官吧?再者说,他举了个很鲜明的例子,他说,你说诗赋只会让人更加奢华,什么叫奢华呢,就是说喜欢那种非常华丽的文章,喜欢那种华丽的文采,他说北宋初期有个人叫杨亿,这个杨亿是个大文人,专写那种奢靡的文章,专写那种华美的文章,他说杨亿这种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杨亿本人是个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并没有因为他写这些东西,他就变得不杰出了。他还举例子,还是北宋初期有个叫石介的,石介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文人,石介的文章写得非常好,道德品质也很高,但是你让他执政、你让他做政治家完全就不行。所以,写不写华丽的文章,写得写不了那样的道德文章,这跟他能不能执政、能不能做一个政治家、能不能干具体的事儿,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的联系,一个人在政治上要表现出怎样的品德,那他在实际的实践当中就会表现出来,这跟他写不写文章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古往今来,能写一手好文章的大政治家那是有的是。没说错吧?那苏轼当然要写出来的东西不大容易让别人能驳得倒,他让别人讨厌的地方也在这儿,主要的观点就是这样,他说就拿现在的这些进士来说吧,天天钻研经史子集,天天钻研道德文章,真让他们上到前线打一仗,真让他们坐到办公室里处理个具体的事情,处理得了吗?你能写道德文章,你能读儒家的经典,你像王安石一样把科举内容全改了,他就一定能够胜任实务操作吗?未必然。当然苏轼自己说这话心也虚,他也没多少经验,这会儿他多大年岁,只是一个年轻的干部。
哎,文章上去,上去之后,神宗看了之后,写得好,我正有这样的疑问,虽然我没考过进士,他当然不用考了,他是招进士的人,但是我早有这样的疑问,今天,你给我一解释,我思想上的疙瘩就算解开了,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专门召见苏轼,你还有什么更具体的意见?就当前的政治形势,可以敞开谈谈嘛。苏轼说没啥谈的,就三条,不知道您爱不爱听,哪三条呢?皇上您现在
“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清·毕沅《续资治通鉴》
什么意思?您现在想要治理天下,心情可以理解,您操之过急,一年的事想在一天里头办成,几代人的事想在您这一代里都解决,太急。听言太广,您什么意见都听,那意见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杂碎,就不能听。您什么都听,听了还都用,这就乱了套了。您进人太锐了,您在人事上放得太宽了,您都用了些什么人,您都不看看?有的人还算是好人,说,那个人还行,那个人底下那人,你不甄别呀?皇上听了以后说,说得有道理,我也觉得有点急,应该慢慢来。
下来了以后就跟王安石商量,王安石一听就不高兴了,说什么呢?什么锐啊、什么广啊、什么急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什么急啊?神宗说要不然把苏轼弄到中书省里头来,让他参与中央文件条例的修订和制定。王安石说这怎么行?我跟这个人在学问上就是两种风格,根本上就是两股道上的人,你让他干点别的吧。干什么啊?让他到开封府去做行政长官,想用那些碎七零八的事把他给困住,让他不要在这儿胡思乱想,不要成天发声,苏轼也没耽搁,在那儿把事处理得好好的,接着发出他的声音,是挺“讨厌”的。苏轼这一生吃亏就吃亏在他这支笔和他这张嘴上,后来他自己也有反省。宋神宗还是很信任王安石的,所以就废除了诗赋取士的这样的制度,当然到后来神宗去世以后,王安石去世以后,这个也都废止了之后,又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你看,科举制度从根本上来讲涉及到人事制度,涉及到干部的培养,在这个问题上,那苏轼跟王安石根本就唱对台戏嘛,他怎么能让王安石高兴呢?王安石也不能说恨死他了,但是肯定是相当地不高兴。神宗就问王安石,说我觉得苏辙跟苏轼这哥俩儿学问比较相近,风格比较相近。王安石说是,他们很相近,他们就是用一些纵横捭阖的学术。什么叫纵横捭阖呢?就像战国的纵横家一样,好空谈,文章写得漂亮,排比句用得多,好放大言,一说就是天下为己任;一说就是天下大事;一说就是纵古论今,但是不靠谱,不论实务,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所以这种人绝对不能用。神宗听了也没有办法,就只好怎么呢?把苏轼安排到开封府去。
解说:在开封府供职的苏东坡,并没有如王安石所愿被日常繁杂琐碎的事务所困扰,他仍然百倍关注王安石,并继续批评变法事宜。接下来,苏东坡还要直接攻击改革变法的司令部,锋芒直指王安石。那么,“拗相公”王安石又会如何对待苏东坡呢?
上元节,其实就是正月十五,宫里边要办灯会,这个办灯会给苏轼提供了一个机会。神宗刚继位不久,想在宫里头开一个比较大的灯节的聚会,想办得好点,就让内务府去采办灯,当时最好的灯叫浙灯,浙江的浙,要采办四千只浙灯,结果去采办之后一问,这价钱特别贵。神宗就说让他们把价钱降下来,我们低价购进。你听着有点别扭,政府如果想扶持商家的话,应该抬价购进才对,你让人家把价钱压下去,是不是?哎,苏轼一听,马上上道奏折,说皇上您不能这么干,这是形象问题,您还不知道多少商家和手工业者就指着您这一把了,想挣点钱。您这下倒好,等了这么长时间,这一把就全灭了,这可不太好,您低价购进,就损伤了商家的利益,而且,神宗为了让这灯会办得好,说了,浙灯只能我们买,老百姓不许买。说这也不对,您得与民同乐啊,您一个人在那穷乐有什么意思啊?您又压了价,还独个儿在那儿乐,这不符合仁义道德,您这样做是不对的,收回成命。
神宗一听,说得有道理,这家伙净说对的,每次提的建议都很适当。苏轼抓住这机会,我还想跟您说说当前的局势,我再跟您说说,他就上了一封奏折说皇上您确实是尧舜之君,就灯这事儿,您一听就吸取了,太伟大了,感动得我热泪盈眶。灯的事儿是小,但由小可以见大,我现在跟您说点大的,现在有人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条例司不好,好好的管钱有管钱的,管兵有管兵的,管政的有管政的,为什么又出来一个独立的机构?没有必要嘛。苏轼说,成立这个机构无非是兴利而除害,可是,如果成立这机构之后,不但没有兴利除害,它本身变成一害的话,那您的麻烦可就大了。他说现在朝廷有点乱,本来呢,就算搞改革变法,也应该是由中书省、由宰相跟皇上您,以及二三重要大臣商议之后才下的政策,可现在所有的政策都从这个奇怪的怪胎一样的机构里头出来,而且很多的政令不从宰相出,从那个翰林学士、从那个副宰相出来,这叫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样下去,国家的政令、法令不能长治久安,不能维持长久。苏轼告诉他,一个国家的存亡根本不在强弱,在于道德;一个国家国运的长短,不在贫和富,在于风俗的厚与薄。
你注意,我没有说苏轼这个话一定是对的,你注意,苏轼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强调了这个问题的另一段,就是说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要维持长久的稳定,就要有长久的、稳定的道德观作为它的基础,就要有长久的、稳定的、淳朴的风俗作为人民思想的基础,人心是不能乱的。他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他没有强调经济基础,他不谈这个,这是他们擅长的做法,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只谈我的,我不谈那个对你有利的。他跟司马光有个共同点,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道德,道德、人心稳定了,什么都好办。如果因为生财乱了人心,一切都谈不上。
王安石看了之后非常讨厌他,开始还是有点觉得不舒服,后来就发展为很讨厌,讨厌上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他待在这儿有点多余。正好这会儿有个事儿,就凑巧了,什么事呢?王安石他的弟弟跟另外有一个官员叫谢景温的妹妹结婚了,所以他们两家是亲戚关系。这谢景温也受到了王安石的提拔,他是一个谏官,谢景温说,我告诉你一个事儿,苏轼的父亲去世了,他回家去奔丧,他去四川,然后从四川再回来不是得走水路吗?他走私,在船上运不该运的东西。王安石一听太高兴了,终于走私了,查他,早就想办他了,找一机会,查来查去,没查着什么实据。把苏轼给查害怕了,苏轼赶紧申请,我不在这儿待了,我走,我不说话了,我走,这么着,苏轼才到了杭州做了通判,相当于杭州市的副市长。你看,我前面这只是举了很小的一点例子,就说明这苏轼,他在诸多的政见上,在改革的变法的这个事情上,他跟王安石之间是有很多冲突,这个冲突发展到最后就是以王安石把他轰走为结果。后边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苏轼在徐州做官;在密州做官;在湖州做官,那会儿王安石已经罢相回家了,他(苏轼)在湖州的时候。后来他不是让人给抓起来了吗?说他在诗文里头抨击新法、抨击朝廷,甚至嘲弄宋神宗。给神宗惹毛了,派人把他抓了起来,投到监狱里头,审了一百多天,放出来了以后,给他发配到了黄州,到了赤壁,写了“大江东去”,还真得感谢改革变法。
解说:政治理念上的不同,使得苏轼对王安石的变法改革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也使得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冲突不断。但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改革变法的起伏波折,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局限于改革变法。那么,这对冤家在私底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交情呢?
苏轼走了一大圈儿,最后跑到黄州去了。王安石中间经历了两次罢相,最后心灰意冷,孩子也死了,自己的学生吕惠卿等人背叛了自己,弄得心情非常糟糕,回到了南京。两个人开始掐了半天,最后变成两个可怜的人。神宗最后起了怜悯之心,想还要再重用苏轼,就把他要调到河南的汝州做团练副使。苏轼在常州买了房子,有地产,跟皇上申请说我去常州,这么着让他去了常州,他在去常州的路上就专程到南京拜访了王安石。
这个东西很奇怪,我们前面讲司马光的时候说,这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相近的地方,也许连他们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这种相同的秉性、个性、思想和道德,却让他们在政治上成了非常尖锐的对立者,而现在苏轼的情况是什么呢?之前有很强烈的对立,现在突然地都归零了,俩人都归零了。归零了之后,两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这就显得非常有意思了,这才更加本质地接近了北宋时期这些最优秀的士大夫和文人的那种个性和气质,以及他们互相之间那种本质的关系。
好了,苏轼被贬黄州。王安石退休在金陵,对苏轼非常关注,有一天从黄州来了一个人,见着王安石就跟他说了,王安石就问他,说最近子瞻有什么新作没有?有什么新的作品没有?说有,走得急,落在船上。说赶快去拿、赶快去拿。赶紧就去拿,是苏轼写的一篇文章,叫《宝相藏记》,写佛教方面的内容。当时天色已经黄昏,还没有掌灯的时节,王安石心情很迫切,就站在屋檐底下,就着黄昏的这个日光,就开始看这篇文章,一边看一边说,子瞻真是人中之龙也。对他非常器重,因为他文章写得太好了,苏轼在黄州写过一首诗,叫《雪》,就是下雪。其中有这么两句,说,
“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苏轼《雪》
王安石就读这两句诗,写得好。他的女婿蔡卞就问他说,好在哪儿啊?王安石说,你来说说这两句是什么意思?蔡卞说“冻合玉楼寒起粟”,玉楼,下雪了,楼变成玉楼了,这是下雪。可为什么把楼给冻起来了,这个很难解释。“起粟”是什么意思呢?粟就是米粒啊,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又说“光摇银海眩生花”,说银海这个也可以说是下雪以后就变成银海了。“光摇银海眩生花”是说雪地里头照人的眼睛晃得慌?王安石说这你就完全不懂了,我告诉你,苏轼在这两句诗里头用了一个典故,典故是道教的,在道教当中把人的肩膀叫做玉楼,把人的双眼叫做银海,所以“冻合玉楼寒起粟”是说天太冷了,冻得肩膀缩起来了,皮肤上都起了小米粒了。“光摇银海眩生花”,雪地里头的雪太洁白了,把我眼睛都炫得发晕。懂了吧?这叫学问。你们都看不出来,我能看出来,为什么?我们俩是同等量级的人物。苏轼自己也承认,这诗写成之后,就这玉楼和这银海,好多人都没看出来,就以为是蔡卞的那种很庸俗的解释,其实不是,用了两个很重要的典故。
苏轼到了金陵,要去见王安石,王安石骑着他那头著名的驴,在江边上等他。苏轼的船就过来了,苏轼从船上跳下来,穿着便装,见到了王安石之后一拱手:
“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曲洧旧闻·卷五》
我呀,今天斗胆,穿着便装,我来见大丞相。王安石看他大笑,世间礼法岂为我辈所设?(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曲洧旧闻·卷五》)我们这样的人还能受一般的礼法约束吗?太客气了。苏轼紧接着说,我也知道我在你的手下没做过什么工作,净起了反面作用。这两个人之间的交往和见面已经不再有那种政治上的恩怨,可能有些芥蒂,但是这样的一种交往,王安石为什么说世间礼法岂为我辈所设呢?就是如果抛开政治的恩怨不谈的话,我们这样的人,那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不是说把世间看穿了,而是我们的学识、我们的修养、我们的道德还有我们的人品,早就在一般的世俗之上,我们在这个层面上现在来进行对话,而不是在那种很窄的关于新法的问题、青苗的问题上再讨论问题了。两个人的身份现在不一样了,政治上归了零之后,真正的文化价值体现出来了,才表现出来了,这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个人走,苏轼就送给他了两句诗,这诗写得很有意思,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従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次荆公韵四绝之三》
说我看见您老先生啊,王安石比他年纪大,骑着那头著名的驴,从那山坡上走过来,渺渺的感觉,很孤独、很瘦小,我就在脑子里想起您当时没生病的时候,咆哮的那个形象,拿着国家天下大事的那样,一种刚坚不可夺其志的样子,看你现在的病容和老态,想起了当年的王安石王介甫。“劝我试求三亩宅,従公已觉十年迟。”王安石说,哪也别去了,咱俩就搭个伴儿吧,你就在南京这儿买上三亩地,盖个宅子,咱俩天天爬爬山、打打球、吟吟诗、喝喝酒,挺好的,一切,神马都是浮云。可是我觉得已经有点迟了,我早知道十年前您是这样,我就在您门下求学了。这意思说得很婉转,说早知道您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又何必呢?他们俩刚见面的时候,王安石就说,好个翰林学士,我可等了你很长时间了。苏轼说,你们老家抚州出一种皮鼓,这个皮鼓很贵,有一位有钱人就要买它,买的时候要试一下它能不能敲响,“梆梆梆敲不响,气得那卖家就把这鼓“咣”地扔到河里头,结果“梆”地一下响了,这卖家就说你早点发出声音来啊,怎么现在才发出声音来啊?这不太迟了吗?买家都走了。他就跟王安石说,您要早发出这声音来,咱俩也没那么多过节了,是吧。这正是像那诗上说的,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题三义塔》
虽然他们不是兄弟,但是现在总能算是知己吧。所以你看,他们两个人应该说在政治上归零了之后,在去掉了或者说暂时去掉了政治上的恩怨之后,开始以文章、以诗文、以道德来相交往的时候,发现是知音。苏轼离开南京的时候,王安石就感慨,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不知道再过几百年还有这样的人,对他的才华是相当地钦佩,相当地器重。
解说:公是公,私是私,政治是政治,友谊是友谊,苏轼和王安石这对冤家之间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光明磊落的胸怀和高尚纯粹的品格。而在康震老师眼里,“拗相公”王安石也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人。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老师为您盘点王安石和政敌苏轼、司马光之间的微妙关系。
你看,我们讲到这儿,你注意,前面讲到司马光的时候我们说,司马光那种个性、气质、品德跟王安石很相近,这是第一。在政治上他们很对立,这种对立不但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混乱,或者让我们感觉到某种恶心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反而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两个伟大人物的身上,在这个时代里边,迸发出了多元的光彩。但苏轼不一样,苏轼的个性、秉性、气质跟王安石是有很大不同的,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也有很多相通之处,这个相通之处是什么呢?是博学、是才华、是诗文。所以你注意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你把苏轼和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三个人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东方不亮西方亮,他们共同的死结是在政治上,是在具体的政见上,甚至他们在根本的政治立场上是完全相同的,就像刚才(上集)我们说,司马光说的我们是殊途同归嘛,都是为了大宋朝,只不过是在如何好的问题上有分歧。所以这个分歧最后在经过了将近一千年以后我们再来看的时候,这个分歧,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已经变得非常小了,说白了就是在大宋王朝那个具体的历史阶段的如何好和强大的问题上,他们有分歧,但从长远的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三个人之间王安石和司马光,在人品、道德、秉性、做人方面是当代之楷模,王安石和苏轼在文章、才华、学问方面也是一时的典范。
那你再结合起来看王安石,王安石他有很多政治上的做法、政策,可能是一时之功利的政策,甚至这些政策有时候还可能伤害到了国家利益,但是从总的、全面的角度来看,王安石这个人在道德、在文章、在事业、在品行、在才华、在博学上,包括在政治事业上,无疑成为了北宋时期首屈一指的一个人物,他跟两个政敌之间都有着非常广泛的交流和沟通的这样的空间,这充分说明王安石并不是一个单面的人,并不是一个僵化的人,相反的,他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人,而且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人,也因此他是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所以这样的人物,我们对他的评价就不能仅仅地局限在政治层面,我们讲政治家的王安石这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从政治的勇气和开拓的精神上来讲,他超过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可能任何一个宰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倒真是应了梁启超的话,他认为王安石是古今第一完人。当然了,梁启超本人是改革家,他这样赞许他的前辈也无可厚非,但即便是我们自己平心而论,就从他和司马光、从他和苏轼的这种交往能够看到,王安石的确是古今以来不可多得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杰出的学问家、杰出的文学家。那么在接下来的篇幅里边,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闲居在家的王安石的形象,这将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现政治家之外、与反对派的对立斗争之外的王安石的风采,相信这个风采能给我们大家一个别样不同的王安石的概念。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