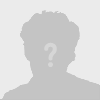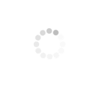|
宋曹《书法约言》的书学思想 宋曹(1620-1701年),字邠臣,一作彬臣、份臣,号射陵,又号射陵子、耕海潜夫、射陵逸史、汤村逸史,亦曾自署淮阳一老、中秘旧史、淮南旧史,盐城北宋庄(今盐城郊区大纵湖乡)人。25岁时由地方官辟荐任南明弘光朝中书舍人,明亡后隐居盐城汤村,筑蔬枰养母。清初二次诏举山林隐逸,宋曹均辞不就征。康熙十七年复举应博学鸿儒选,亦坚谢不赴。 郑培凯《明末清初的文化生态与书法艺术》中云:“强调改朝换代的天崩地解带来剧烈心理震撼,激发了一些人的文化关怀与艺术潜能,产生不受拘牵的独特面貌,是合理的解释……”。明末清初的书坛面貌令人炫目,浪漫书风、遗民书法以及碑学的滥觞均在这期间登场,书法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时期出现如此众多的风格各异,极具个性的书家,从徐渭、董其昌、到张瑞图、倪元璐、王铎、傅山,这些人的艺术探索,即袁宏道所谓“独抒性灵”之体现,放在书史内在发展的脉络来看,他们所追求一种刚健浑厚,反对柔靡机械,这代表明代帖学以二王、赵孟頫为宗的风气逐渐走向衰微,清早期,尤其是康、干之间董、赵面貌笼罩下帖学陷入了“馆阁体”的牢笼,渐趋单调与乏味,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也给碑学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宋曹的书学理论著作《书法约言》正是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该书自康熙三十六年被张潮(1650-1707年)收入《昭代丛书》以来,影响深广,为清初重要的书学论著作。曹溶(1613-1685年)评其:是论如烂漫春花,远近瞻望,无处不发。可谓书家三昧。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三《通论》中云:“射陵夙以能书称,是编首为总论两篇,不作浮词,至为扼要”。阮葵生(1727-1789年)在《茶余客话》中亦云:
宋射陵书一时负盛名,所著《书法约言》颇得古人神髓。后来香泉、坛长、补之、湘帆辈纷纷论辩,皆不及也。
清早期较为重要的书论中,冯班(1602-1671年,字定远,号钝吟)所著《钝吟书要》、笪重光(1623-1692年)《书筏》、杨宾(1650-1720年)《大瓢偶笔》、王澍(1668-1739年)《论书剩语》包括稍晚的何焯(1661-1723年)《义门题跋》在体例上皆为评论、题跋之类的文字,缺乏一个系统完整的结构,有些斤斤于执笔之法以为至宝,有些议论则明显偏颇失妥,如杨宾恶评论杨凝式,冯班于宋人书仅推许蔡襄,于明人书则绝不许肯,这在今天看来,其观点似乎略显狭隘。而宋曹《书法约言》为通论性质的文字,除了略叙书体变迁之迹以及楷书、行书、草书的临摹创作方法外,还涉及书法的审美、品鉴等诸方面。对于同时代人过分注重于执笔之法,宋曹仅以数语带过,且言简意赅,其云:大要执笔要紧,运笔欲活,手不主运而以腕运,腕虽主运而以心运。对于不同的书体,提出不同的学习方法,如草书、行书、楷书比较科学。《书法约言》中所蕴涵的书学美学思想更是值得我们深作研究。《书法约言》的美学思想以继承前人为主,在对古代书论进行了综合的把握之后,广采博收,从孙过庭的《书谱》到黄庭坚的《山谷题跋》,近到董其昌《容台集》中的书论,宋曹摘其精华,加以整合,其中尤以对“神采”说的发挥犹为精彩,其云:
凡作书要布置,要神采。布置本乎运心,神采生于运笔,真书固尔,行体亦然。
有关神采的观念,南朝王僧虔《笔意赞》中就云:“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到唐代张怀瓘论书发展到“唯观神采,不见字形”,神采被强调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书法神采,首先体现在气韵上,气韵是贯穿在整幅作品中的一种精神境界。这里的“不见字形”决不是不要字形,而是通过字形去探寻比形质更重要的东西。书法艺术是形与神的合一,表现形质的笔法,墨法,布白等只是手段,写神才是最终目的。事实上,形、法的束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从而人们必然寻求新的突破,从而满足人们“达情抒意”的需要。但神采与气韵、意境等都是无形之物,需要通过有形的用笔、结构与章法加以表现。宋曹早就看出了其中的关系,他指出“规矩既失,神则无存”,并云:
若一味摹仿古人,又觉刻划太甚,必须脱去模拟蹊径自出机杼。渐老渐熟,乃造平淡,遂使古法优游笔端,然后传神。传神者,必以形,形与手相凑而忘神之所托也。
其实,形与神的问题,从南朝以来一直是中国古代书、画家非常关注的焦点,北宋苏东坡说出了“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著名论见后,“神采”被当成书画“神品”的最基本条件,也导致了部分书家过分强调自抒胸臆,走向了无质无形,惟求神采的极端。形与神是一对矛盾的统一,失去一方,另一方就不可能存在,神必须依赖形以存,舍去了形,神就几乎成了水中月、镜中花。所以宋曹又云:“肋骨不立,脂肉何附;形质不健,神采何来”。
对于书画中的“生”与“熟”的问题,董其昌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云:“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宋曹受其影响,但不仅仅生搬硬套,而是以一个纯书家的立场对其进行逻辑上的阐释,指出“生”有先“生”与后“生”之分,“生与熟”之间的辩证关系被他发挥的淋漓尽致,更加客观,也更符合一般书家的学习成长规律。其云:
书必先生而后熟,既熟而后生。先“生”者,学力未到,心手相违;后“生”者,不落蹊径,变化无端。
先“生”乃学习古人,是取法经典的起步阶段,后“生”才是追求自我,表现个性的终级目标,“生”何以求?“生”何以美?如果不把这层关系给理顺,那真理就会越辩越糊涂。这里面的关系,就是即所谓的“入古”与“岀古”问题。他在《论草书》一节中已很好地为其作了注解,云:“必以古人为法,而后能悟“生”与古法之外。悟“生”与古法之外,而后能自我作古,以立我法也”。
而最能代表宋曹书法美学思想的则是“四贵四不”,即“笔意贵淡不贵艳,贵畅不贵紧,贵涵泳不贵显露,贵自然不贵作意”。这样的审美观念乍一看,也是综合了傅山的“四宁四毋”说与董其昌的“淡说”一路,但如果仔细推究起来,也是明末清初书坛大势所然。明末浪漫主义书风在入清后可谓是强弩之末,继王铎、傅山后,由于清初的满族皇帝个人胃口的偏好,导致了董其昌、赵孟頫书风在一段时间内笼罩全国,结果是,学董、赵之人,清淡高逸之妙不曾学到,董、赵之柔弱学得满身。董、赵虽柔而不俗,学者却难免一俗。清初童子学习书法也基本是受时人的影响和左右,如当时名气甚大的常熟冯班父子、金坛蒋衡父子等,在他们的影响下,师徒相授,近亲繁殖,学子们眼界遂为所囿,亦步亦趋,守而不变成法,使得清初的帖学从起步阶段就误入歧途,严重阻碍其健康发展。加之馆阁体的盛行,如此导致的恶性循环,导致清初书坛的萎靡现状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草书贵通畅,下墨易于疾,疾时须令少缓,缓以仿古,疾以出奇,或敛束相抱,或婆娑四垂,或阴森而高举,或脱落而参差,勿往复收,乍断复连,承上生下,恋子顾母,种种笔法,如人坐卧、行立、奔趋、揖让、歌舞、擘踊、醉狂、颠伏,各尽意态,方为有得。若行行春蚓,字字秋蛇,属十数字而不断,萦结如游丝一片,乃不善学者之大弊也。
尽管这些论述并不带有多少新意,但从以上的几行文字明显可以看出宋曹的书学观念是崇尚古意,但又不拘于成法,他是属于清初少有的几个善于思考的书家之一。他深深知道馆阁体之类的实用书法与书法艺术的区别,他明白“肇于自然”的书法艺术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的整个心灵,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各个方面。
张潮为《书法约言》所作的跋,正可拿来作为本文的结语:
射陵向以此帙赠余,不知为何人所携去。余复索之于其小阮汝吉,汝吉未有以报,而射陵邮寄陈子定九中,适有此帙。定九转以见示,余得之不啻法宝,亟载入丛书中,以与世之工书者,其共欣赏焉。(佚名) 博主链接(一) 宋曹《书法约言》节录—— ○论楷书
盖作楷先须令字内间架明称,得其字形,再会以法,自然合度。然大小、繁简、长短、广狭不得概,使平直如算子状,但能就其本体,尽其形势,不拘拘于笔画之间,而遏其意趣,使笔笔著力,字字异形,行行殊致,极其自然,乃为有法。仍须带逸气,令其萧散,又须骨涵于中,筋不外露,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方是藏锋,方令人有字外之想。如作大楷,结构贵密,否则懒散无神。若太密,恐涉于俗。作小楷易于局促,务令开阔,有大字体段。易于局促者,病在把笔苦紧,运腕不灵,则左右牵掣。把笔要在虚掌悬起,而转动自活。若不空其手心,而意在笔后,徒得其点画耳,非书也。总之,习熟不拘成法,自然妙生。有唐以书法取人,故专务严整,极意欧、颜。欧、颜诸家宜于朝庙诰敕。若论其常,当法锺、王,及虞书东方画赞、乐毅论、曹娥碑、洛神赋、破邪论序为则,他不必取也。
○论行书
凡作书要布置、要神采。布置本乎运心,神采生于运笔,真书固尔,行体亦然。盖行书作于后汉刘德昇。魏锺繇亦善作行书,所谓行者,即真书之少纵略。后简易相间而行,如云行水流,秾纤间出,非真非草,离方遁圆,乃楷隶之捷也。务须结字小疏,映带安雅,筋力老健,风骨洒落。字虽不连,而气候相通,墨纵有馀,而肥瘠相称。徐行缓步,令有规矩;左顾右盼,毋乖节目。运用不宜太迟,迟则痴重而少神。亦不宜太速,速则窘步而失势。布置有度,起止便灵,体用不均,性情安托!有攻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攻,神采不变。若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笔,无机智之迹,无驰骋之形。要知强梁非勇,柔弱非和;外若优游,中实刚劲,志专神应,心平手随,体物流行,因时变化,使含蓄以善藏,勿峻削而露巧。若黄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风穆穆然,如此作行书,斯得之矣!又有行楷、行草之别,总皆取法右军禊帖、怀仁圣教序,大令鄱阳、鸭头丸、刘道士、鹅群诸帖,而诸家行体次之。
○论草书
汉兴有草书,徐锴谓张并作草,并草在汉兴之后无疑。迨杜度、崔瑗、崔实草法始畅。张伯英又从而变之。王逸少力兼众美,会成一家,号为书圣。王大令得逸少之遗,每作草,行首之字,往往续前行之末,使血脉贯通,后人称为一笔书,自伯英始也。卫瓘得伯英之筋,索靖得伯英之骨。其后张颠、怀素皆称草圣,颠喜肥,素喜瘦,瘦劲易,肥劲难,务使肥瘦得宜,骨肉相间,如印泥画沙,起伏随势。笔正则锋藏,笔偃则锋侧。草书时用侧锋,而神奇出焉。逸少尝云:作草令其笔开,自然劲健,纵心奔放,覆腕转促,悬管聚锋,柔毫外托,左为外拓,右为内伏,内伏有度,始为藏锋。若笔尽墨枯,又须接锋以取兴,无常则也。
然草书贵通畅,下墨易于疾。疾时须令少缓,缓以仿古,疾以出奇,或敛束相抱,或婆娑四垂,或阴森而高举,或脱落而参差,忽往复收,乍断复连,承上生下,恋子顾母,种种笔法,如人坐、卧、行、立、奔趋、揖让、歌舞、擗踊、醉狂、颠伏,各尽意态方为有得。若行行春蚓,字字秋蛇,属十数字而不断,萦结如游丝一片,乃不善学者之大弊也。古人见蛇斗与担夫争道,而悟草书。颜鲁公曰:张长史观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与公孙大娘舞剑器,始得低昂回翔之状。可见草体无定,必以古人为法,而后能悟生于古法之外也。生悟于古法之外,而后能自我作古,以我立法也。
射陵逸史曰:作行草书须以劲利取势,以灵转取致,如企鸟跱,志在飞;猛兽骇,意将驰。无非要生动,要脱化。会得斯旨,当自悟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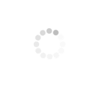
博主链接(二) 宋曹的“以临代创” 宋曹的书法作品中,主要包括楷书、行书、草书和少量的隶书,其中尤以行草书为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分作品中,内容上除书写自作诗外,大部分为临帖作品,临写对象有《淳化阁帖》中的二王作品、孙过庭《书谱》等。形式上以2米左右的高堂大轴居多。
将《阁帖》放大,以临摹代替创作,在明末清初曾一度风靡,傅山、许友等人均有此类作品传世,但存世鲜见。王铎的传世作品中,此类形式占了大半。而在宋曹存世可查的七十多件书法作品中,此类作品亦达到了三十几幅之多,所占比例与其惊人相似。
宋曹的临帖作品,注重意临,以不囿于古人,不拘于形似为旨,故而能另辟蹊径。临写的对象以晋、唐书家作品为主,其中临写《阁帖》中二王的行草书和孙过庭《书谱》居多,此幅作品节临孙过庭《书谱》,纵122厘米,横29厘米,现为天渡楼薛翔先生藏品,作品裱式为日本裱法,是从海外回流的一件宋曹书法的精品。作品通篇布局灵动飞纵,用笔敦实厚重,圆劲中尽显骨力,绵里裹铁,绝无花哨。用“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来形容,可谓再贴切不过了。宋曹自己认为草书“瘦劲易,肥劲难”(《书法约言》),所以他的草书也经常以体态略肥,缓多疾少的面貌出现。在他的这幅临帖作品中,字形宽博、笔画厚重,结体呈内敛团势,带给我们“肥劲”的感觉尤为强烈。对于宋曹的书法风格,清人杨宾(1650~1720年)云:“余书与时流相较,气概不如宋射陵父子,间架不如冯补之……宋射陵父子,虽有毡裘气,然亦江北之杰也。”(杨宾《大瓢偶笔》卷六)指出宋曹书法以气概胜,虽有所谓的“毡裘气”,使他的作品展现出更多的北方书风所具有的粗犷、豪迈之气,以气势征服观众,审美上追求“古”、“雅”、“健”,这种风格明显迥异于清初董、赵笼罩的时风。
王铎曾云“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从宋曹留下的大量临帖作品来看,他的创作状态也基本类似,但临摹《阁帖》只是他的手段,崇尚古风,敬畏经典,最终从临摹中蜕化才是他的目的。正如他在《书法约言》中所云:“若一味摹仿古人,又觉刻画太甚,必须脱去模拟蹊径,自出机杼”。邱振中先生对宋曹的评价至为中肯,其云:“宋曹书法具有一种清初书坛少见的质朴、刚健,并由此而真正接近了人们所向往的古风”,诚为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