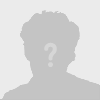|
欧美文学导论
·上编
从古希腊到18世纪,欧洲文学处在发生和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经历了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特定的社会结构形态,为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条件。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先后出现了人文主义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等基本相同的文学现象,形成了欧洲文学史上流派更迭、思潮相继的基本发展模式。古希腊文学和希伯莱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流,文学史上称为“二希”传统,它们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呈矛盾冲突和互补融合之势。欧洲近代文学的人文观念和艺术精神的基本内核,都来自于这两大传统。
古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源头之一,其中所蕴含的“人”的思想观念,经由古罗马文学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希腊民族对“人”的重视,与该民族人的自然观、宇宙观有密切联系。古希腊人同自然分离后,就产生了强烈的个体意识,作为主体的人就处在高于自然与社会的位置上,主张人对自然与社会的征服和改造,主体与客体呈分立态势。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人智),是古希腊文化的本质特征。在这种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古希腊文学,就呈现出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特征,具有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古希腊神话是原始初民的自由意志、自我意识和原始欲望的象征性表述。在神话中,神的意志就是人的意志,神的情欲就是人的情欲,神就是人自己;神和英雄们恣肆放纵的行为模式,隐喻了古希腊人对自身原始欲望充分实现的潜在冲动,体现了个体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执著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稍晚一些时候的古希腊悲剧中,英雄们总是因“命运”的重负而深感行动的艰难,但又从不放弃行动的权利,敢于反抗“命运”的捉弄。这种困兽犹斗的抗争,体现出了个体生命的无穷追求与“命运”的不断惩罚之间的矛盾构成的悲剧意识。这一时期的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学对人性的发掘也就进入了新的阶段。总之,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虽然其中也不乏理性精神,但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对人的肯定上,而不是与原欲相对意义上的理性意识和道德规范。
古罗马文学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古希腊文学中的人本意识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并经由古罗马文学广泛地流传于后世的欧洲文学与文化之中。不过,古罗马人自身独特的文化性格,又使他们的文学带有自己的独特性。古罗马人崇尚文治武功,对人的力量的崇拜常常表现为对政治与军事之辉煌业绩的追求,由此又演化出对集权国家和个体自我牺牲精神的崇拜。因而,古罗马文学比古希腊文学更富有理性意识和责任观念,在审美品格上更趋向于庄严和崇高的风格。但是,古罗马文学人文观念的主体依然是古希腊文学的人本
意识,仍属于古希腊原欲型文化的范畴。
希伯莱文学是欧洲文学的又一源头,其中所蕴含的“人”的思想观念,经由中世纪基督教文学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希伯莱文化是一种重灵魂、重群体、重来世的理性型文化。从“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角度看,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中相对于原欲而存在的又一层面;原欲与理性是人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因此,古希腊文化与希伯莱文化各自蕴含着人性中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侧面,因而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既对立又统一,既矛盾冲突又互补相融的。在公元1世纪中叶到2世纪末叶的“希腊化”时期,希伯莱文化与希腊文化出现了第一次矛盾冲突与互补融合,希伯莱文化吸收了古希腊文化的某些成分后,演变成一种新形态的文化——基督教文化。此时古希腊文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希伯莱文化,因而,基督教文化是以希伯莱文化精神为主体的,属于希腊的异质文化。
基督教文学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它的人文观念自然大大有别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其中蕴含的是一种理性化的人本意识,或者说是一种宗教人本意识。基督教文学中的英雄,不像古希腊文学那样是人化了的神,而是神化了的人:他们往往因神性的附着才显得威力无穷,而不是因人智的充分显现才显得神通广大;人的欲望被来自于神的那种理性制约着,他们的形象虽显示出了神的崇高,却缺少人的灵性与生机,使人性变得苍白与贫乏。如《圣经》中摩西的形象,其丰功伟绩的建立,俨然是上帝的神力在他身上的显现,是人向神的飞升,而不是神向人的还原。基督教文学中人让位于神、“灵”取代“肉”的现象,表现了人对上帝
的崇拜。此外,《圣经》中的英雄身上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和对民族、群体的责任观念,这种精神与观念又进一步升华为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这是宗教人本意识的又一种体现。总之,重视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质,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早期希伯莱文学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这种尊重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是以后欧洲文学与文化内核的又一层面。
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的大转型时期,人们对宇宙、社会和自我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这一时期,欧洲文化的古希腊古罗马源流与希伯莱基督教源流形成了比“希腊化”时期更大规模的矛盾冲突与互补融合,从而带来了文学中人文观念的重大变化。
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文化走向极端,成为人性的反动,成为人的异己力量,一些人文主义者借用古典文化向它发起了攻击,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希伯莱文化形成冲撞之势。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它的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人性反神性、以个性自由反禁欲主义的思想,是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相冲突的。以人为本和以神为本,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希伯莱基督教文化冲突的焦点。以人为本,归根结底是要求以人性、人智取代神性、神智,从上帝那里找回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也即人自己,因而,这种冲突实质上也就是原欲与理性、肉体与灵魂的冲突。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对基督教文化思想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胜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艺复兴是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它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即原欲与理性、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作了调整,从而有了“人”的觉醒与解放。这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适应性自我调整。当然,文艺复兴运动中既有两种文化的对立与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与互补的一面,因而,人文主义绝不只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它同时又吸收了希伯莱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如原始基督教和《圣经》本身所倡导的仁爱、忍让、宽恕等博爱思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希伯莱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这两种文化都是在人类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们各自都有其发乎人性、合乎人性和违背人性、危害人性的积极与消极因素,因而都有其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所起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它们当中任何单一的文化范式都不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反映,因而也不是人类发展所需要的合理的文化模式,只有两者的互补融合才有可能导向正确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便是重新选择文化模式的契机。
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不同国家的人文主义文学中所蕴含的人文观念,正是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在文学中的不同形态的表现。薄伽丘的《十日谈》把人的原欲作为天然合理的东西加以描写,让人们去追求现世生活的无穷欢乐,表现出“人”的回归与主体意识的觉醒。拉伯雷的《巨人传》中,“巨人”的形象表明了人与神的易位,人取代了上帝,人智的力量是无穷的。小说中“做你所愿意做的事”的名言虽不无偏激,但表达了从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对自由的热切向往。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的追求意识,表达了觉醒的人们要求找回中世纪被压抑的自由天性和人格力量的强烈渴望。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化和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对人的理解的深刻性要远远超过前辈人文主义作家。他早期的喜剧和历史剧,主要表现个性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这和欧洲早期人文主义作家的思想是基本相似的。他的悲剧则表现出文艺复兴晚期欧洲人的迷惘与困惑,更明显地反映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希伯莱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莎士比亚对人的理解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人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人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作出准确的把握。哈姆莱特的犹豫、延宕、忧郁,正是当时人们面对这多重矛盾时两难心态的艺术化表征。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刚刚从宗教的重压下站立起来的“人”,在精神上与上帝依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俗人本意识和宗教人本意识在他身上的融合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正是近代欧洲文化模式的典型形态。
17世纪的欧洲讲究理性与秩序,西欧一些国家相继爆发内战和宗教战争,一度混乱的社会现实使人们意识到理性、秩序的重要性。也就在这个时期,牛顿、哥白尼、莱布尼兹等人的自然科学成果告诉人们,宇宙是井然有序的,因而,社会也应有自己的规范与秩序,个体的人的自由必须合乎或服从于社会规范,而不是一味地“做你所愿意做的事”。哲学家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把人的自我意识、人的思维和理性作为人的本体来看待,赋予人的理性至上的地位。在这种精神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古典主义文学,便以理性作为自己的生命。这种“理性”除了特定的政治内容外,主要指人的思维能力和人的理智。它与中世纪的宗教理性相比,更注重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能动性而否定了神性,这是对宗教蒙昧主义的进一步否定;相比于人文主义思想,它更注重人的理智对情感欲望的制约,强调了对自由的理性规范,这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个性自由的极端现象的反拨。在这种理性主义原则指导下,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通常都处于理智与情感、个人欲望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矛盾纠葛之中,并最终让理智战胜情感,让个人欲望服从国家民族利益,而服从王权则是最高的理性。古典主义文学中蕴含的是一种理智化了的人本意识,它既肯定人的自我意志和主体精神,又强调理智对自我的约束。因而,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更疏远了与上帝的联系,也显得更理智、冷静和成熟,但也缺少热情、缺少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
18世纪启蒙文学的“理性”在肯定笛卡儿所讲的理性精神外,又从自然法则的高度,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的社会法则,肯定人的自我情感的天然合理性。这既是对中世纪宗教神性的更彻底的否定,又是对否定情感自由的古典主义理性精神的一种调节与反拨。启蒙文学家大多都把个性与情感自由强调到了高于理性与秩序的程度。卢梭是启蒙文学中崇尚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典型,他否定了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和美的,因而一切发自自然人性的欲望与要求都是合理的,而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却是人性的污染物和罪恶的孳生地。他的《忏悔录》彻底剥开了包裹在人性外面的宗教的和传统道德的遮羞布,还其自然纯真的本来面目,说明了真正值得人崇拜的是人自己而不是上帝。他的《新爱洛依丝》则是一曲心灵自由与情感自由惨遭厄运的悲歌,是对自然人性的热烈呼唤。歌德则比他更现实、更理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寻找着情感与理性统一,寻找着既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又不与外在客体冲突,既满足个人欲望,又不违背社会道德律令的两全其美的道路。然而浮士德一生执著地探索与追求,最终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这正是歌德对“人”的理解与认识的困惑。但歌德通过对浮士德的描写,把对“人”的问题的探索推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启蒙文学对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性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
欧美文学史导论(上编)
特别重申:本篇文档资料为 “好网角收藏夹” 注册用户(收藏家)上传共享,仅供参考之用,请谨慎辨别,不代表本站任何观点。
好网角收藏夹为网友提供资料整理云存储服务,仅提供信息存储共享平台。
如发现不良信息删除、涉嫌侵权,请 点击这里举报 ,或发送邮件到:dongye2016qq.com。
如发现不良信息删除、涉嫌侵权,请 点击这里举报 ,或发送邮件到:dongye20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