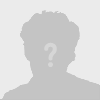。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
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
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
摘要
(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
(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一,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
(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1993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
2,家庭暴力(Domestic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3,性骚扰(sexual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争并予以解除。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二,扩展性别暴力(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状态,威胁着。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方刚,2012:200-209)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2)强奸(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标准的女性。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针对。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女人和女童的歧视,。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受暴者,但(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而女同性恋,则因为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 2011年(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此文发表于《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性别暴力内涵的扩展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 召集人 摘要 本文梳理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等概念的产生及内涵,提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进一步扩展性别暴力的内涵,以使之符合时代需要,并且真正涵盖尽可能多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结合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咨询中呈现出来的信息,笔者在肯定女性是性别暴力的主要受害者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性别暴力应该同时关注家庭暴力、性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同志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提出性倾向暴力、性别气质暴力、性别选择暴力(针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暴力,均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应该成为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关注的对象。 关键词:性别暴力,家庭暴力,男性,性倾向暴力,性别选择暴力 如果从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算起,人类社会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简称性别暴力)的关注已经30多年了。其间,对于性别暴力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笔者主持“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在热线咨询工作中,深刻体会到,我们对性别暴力内涵的理解有待进一步扩展。 一,关于性别暴力的现有定义 在国际文书和媒体报道之中,经常能看到性别暴力、针对妇女的暴力、以及家庭暴力等概念。虽然这几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他们的内函和外延各有不同,不应混淆。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些已有定义。 1,“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与“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Violence) 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1年9月3日在第二十个国家批准这项公约之后,它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开始生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条为本公约的目的,“对妇女的歧视”一词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公约第六条也强调“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 1992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此建议将“基于性别的暴力”纳入到“对妇女的歧视”的范畴中,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严重阻碍妇女与男子平等享受权利和自由的一种歧视形式”。建议明确了“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它包括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威胁施加这类行动、压制和其他剥夺自由行动……”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第8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首次明确提出了“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againstWomen)的概念,界定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宣言还详细列举了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包括:(a)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b)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c)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第8条写到:“我们重申承诺:致力于男女的平等权利和固有的人的尊严以及《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其他宗旨和原则,并奉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发展权宣言》”。第29条“我们决心:防止和消除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在“战略目标与行动”中,提到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是指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基于性别原因的任何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妇女受到身心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也包括威胁采取这种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 第114条补充到:“对妇女的其他暴力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有步骤的强奸、性奴役和强迫怀孕”。 第115条写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胁迫/强迫使用避孕药具、溺杀女婴和产前性别选择”。 第116条同样强调:“某些妇女群体,诸如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妇女、难民妇女、移徙妇女、包括移徙女工、农村或边远地区的贫穷妇女、赤贫妇女、收容所的妇女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流离失所妇女、遣返妇女、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以及处于武装冲突、外国占领、侵略战争、内战、恐怖主义包括劫持人质等局势中的妇女也特别容易遭受暴力行为”。 2006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义为,基于社会定义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违背一个人的意愿对其造成的任何伤害的行为。 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基本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性别暴力”、“针对妇女暴力”这两个概念。 2,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与伴侣暴力(MateViolence)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中提到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形式的第一条,便是家庭暴力: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1995年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美国各州关于家庭暴力内涵的规定大都与全美未成年人和家事法院法官联合会于1994年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第102条的规定一致。该《法典》第102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损害或试图损害其他家庭成员之身体权益的行为;使其他家庭成员陷入对受有人身损害的恐惧之中的行为;使用武力,武力威胁或胁迫手段,违背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与之发生性关系。” 在新西兰,1995年通过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 “家庭暴力”一词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才进入中国的。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提到了“家庭暴力”。该法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01年12月2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进行了具体界定,该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它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2008年.全国妇联、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印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也延袭了这一定义。 这一定义被学者们普遍认为定义过窄,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限定于身体暴力,性暴力没有被纳入,精神暴力没有被具体化,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暴力均被排除在外。(吕频,2011:12)而依据前述联合国各相关国际公约及国际共识,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精神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 《婚姻法》以伤害后果衡量施暴方的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不利于保护受暴人权益。关于心理暴力的伤害性,有学者指出:“心理暴力,是指施暴人威胁要伤害受暴人或当着她的面砸东西、折磨宠物、自虐或自杀等,使受害女性在心理上产生恐惧,进而被迫顺从施暴人。”精神暴力虽然暂时没有看得见的身体伤害,但累积的精神伤害,同样会使受暴人出向身体症状,即所谓“心理问题身体化”,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睡眠障碍、不明原因的头痛或浑身酸痛,等等。(陈敏,2007:9-11) 第二,《婚姻法》将家庭暴力严格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不能涵盖所有的受暴人。学者们主张借鉴相关的国际文件,扩大家庭暴力的定义。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将“家庭”的概念扩大化,既包括家庭成员,指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和现行法律中规定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含夫妻双方的)、子女及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姑侄等,也包括“视为”家庭成员的,即前配偶、同居者(含婚外同居的)、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如恋人(含同性恋者)。(吕频,2011:97-98) 联合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范本框架》对各国制定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提出了指导要求,对妇女家庭暴力立法范畴的关系包括:妻子、同居者、前妻或前同居者、女友(包括不同居一处的女友)、女性亲属(包括但不限于姐妹、女儿、母亲)和家庭女佣。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3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这样定义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或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行为”,其中家庭成员指“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或曾经有过配偶、同居关系的人,视为家庭成员”。(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2005: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制定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2条提出了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本指南中的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主要是夫妻之间,一方通过暴力或胁迫、侮辱经济控制等手段实施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性、精神等方面的人身权利,以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的行为。同时该指南第三条规定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身体暴力是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暴人、或限制受暴人人身自由等使受暴人产生恐惧的行为;性暴力是加害人强迫受暴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暴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暴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暴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暴人自尊心、自信心或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基于对家庭暴力对象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伴侣暴力”代替“家庭暴力”。伴侣暴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对象的理解。本文后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交替使用伴侣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不同概念。 3,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 2001年联合国宪章特别设立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5次会议指出,所有形式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骚扰都削弱了妇女享有的人权,并进一步揭示性骚扰与人的尊严与价值不相容,应与之斗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针对女人和女童的歧视,在拐卖男婴和男童时反而成为对男孩子性别暴力的根源。 需要再度强调的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性别暴力中最主要的问题,它一方面反映出权力控制和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各种健康、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也严重限制了妇女的平等参与。性别暴力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暴力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妇女、女童、男人和男孩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暴力的受暴者,但性别暴力的受暴者无疑大多数为妇女和女童,这是由于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导致的。 笔者对于性别暴力加害人与受暴人内涵的扩展,无意否定上述事实,只是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还存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在我们思考性别暴力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以生理性别为思考标准,而应该以社会性别作为定义性别暴力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对“生理人”的解构。 四,针对性与性别多样性的性别暴力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男人和女人的二元性别划分方式上来思考性别暴力,而应该充分考虑进其它性别的存在。忽视其他性别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性别暴力。事实上,其它性别所受暴力更被视为理所当然、明正言顺。 1,针对性别气质的性别暴力 这是针对不够阳刚的男性,以及不够温柔的女性的暴力。前者被称为“娘娘腔”、“二尾子”,后者被称为“男人婆”、“假男人”。不同于主流的二元划分的,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气质的操演,因为破坏了“规则”,而成为施暴的对象。当有学者认为男孩子不够阳刚了,因而提出“拯救男孩”的时候,当全社会倡导女孩子要做“淑女”的时候,不正是一种公共空间中蔓延的性别暴力吗?这种暴力同样制约着正忠实地执行性别二元划分规范的性别操演者,如果你敢越雷池一步,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暴力对待的对象。于是,主流社会的人按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拼命地表演成一个男人或女人,同时更突显了性别气质多元实践者的“变态”。 谁在对性别气质的“出轨者”施暴?背后是文化,具体的实施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甚至是国家体制。无论哪种性别的人,都可能成为歧视、打击本性别或另一性别中不符合主流社会性别规范者的力量。“娘娘腔”的男人与“男人婆”的女人,会成为不同男人和女人共同歧视的对象。要求男人“像个男人”的,不只是男人,更可能是女人。在女性内化了传统性别观念时,会因为男性“没本事”、“窝囊”而对他实施精神或肢体暴力,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公共空间。此外,鼓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同时,也是对不符合这一性别气质的人的暴力,当教育系统强行推行这一性别刻板模式的时候,便是一种国家暴力。 2,针对性倾向的性别暴力 针对同性恋者的各种暴力,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疑属于性别暴力的一种。 男同性恋者被认为不够符合阳刚之气,恐同与反同势力一直强调男同性恋者的“女性气质”,虽然事实上女性气质并不是所有男同性恋者的共性,而且女性气质并非“坏”的。恐同者认为,男同性恋者不再“干女人”,而是“互干”,这是无法忍受的,说到底,男同性恋的存在是对传统的支配性阳刚男性气质的一种挑战,是对致力于捍卫这种男性气质的男人的示威。 而女同性恋,则因为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不再附属于男性,从而为男性暴权所无法容忍,所以不难理解会有通过强奸来“治疗”女同性恋的论调和行动;另一方面,女同性恋的存在也让一些异性恋的、尊重男性霸权地位的女性觉得自己是被公然挑战的。 针对同性恋者的肢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从来都不缺少。这些表面是对性倾向的歧视与偏见,实则是基于性别的暴力。 3,针对性别选择的性别暴力 针对性别选择的暴力,主要指针对跨性别及生理间性人的暴力。跨性别(transgender),指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跨性别者包括:变性欲者,变性人,易装者,跨性别表演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只做了隆胸手术的生理男人,基于性别选择目的做了乳房切割的生理女人,以及其他所有认为自己不属于传统观念关于男人和女人定义的人。跨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这也要求我们对性别暴力进行新的探索。生理间性人(intersex,又译双性人)一度被归入跨性别,但随着生理间性人解放运动的开展,他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被归类于“他者”,而视自己为独立的一种性别。 逾越了传统性别分类与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只不过,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及改变的病人甚至罪人,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生理间性人,曾被理所当然地在其出生之后便被医学“解决”,从而成为被“屠杀”的一个人种,不承认他们有存在于世界上的权利。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定义指出,暴力可能是发生在私领域,也可能是发生在公领域,甚至可能是国家默许的,无论发生在何种领域。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同样可以非常好地解释国家默许。 对跨性别与生理间性人的歧视与暴力随处可见:媒体充斥着对跨性别者与生理间性人偏颇、好奇的报道;公共卫生间只分男女,令跨性别者难以选择;《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以“易性癖”、“易装癖”、“变性癖”等对跨性别进行疾病化、病理化的定义;心理咨询师及精神卫生工作者将跨性别者的性和性别取向作为精神或心理疾患进行“治疗”;社会对跨性别者的污名化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国家规定的变性手术的限制,影响了他们性别的自主选择;医疗保险未能将变性手术视为“医学需求”,使其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福利;医生或父母在未经过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对生理间性人进行无法逆转的旨在改变其性别的干预;跨性别者求学、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经常受到侵犯;…… 2011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各会员国在第17届会议中投票通过了关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人权决议,这在联合国大会或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议“对于在世界所有地区,针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与歧视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在世界所有地区,国际人权法适用于“基于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基于性别认同的暴力,当然属于“基于性别的暴力”,属于性别暴力研究者与行动者干預的目标。 五,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制止针对妇女暴力,需要男性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将男性视为铁板一块的施暴者。男性内部也存在差异性,也可能成为暴力的受暴人,忽视这一点,忽视男性的权益,会阻碍推进男性参与。 此外,在同性恋运动、跨性别及其它性别多元运动积极开展的今天,反对性别暴力不能忽视针对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从略) 性倾向、性别气质与性别多元的暴力。反对性别暴力需要实现最广大的同盟,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所有受性别暴力对待的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这不仅将提升对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非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的重视,还将使反对性别暴力的目标真正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得以实现。
争并予以解除。 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公约》第19号一般建议指出:“性骚扰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对妇女的一种歧视形式”。第19号建议进一步强调指出,性骚扰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例如身体接触和接近、以性为借口的评论、以文字或者行为表现出来的与色情和性相关的要求。 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认为性骚扰是指非本人愿意的性关系,它包括侮辱评论、开玩笑、暗示等以及对人衣着打扮、体形、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不适当的品评等;有损人的尊严的故意讨好或家长式的伤害人的尊严的态度,不管是否伴随威胁;与性相关联的淫荡的表情或姿势;无必要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爱抚、拧捏或者伤害等。 我国学者也界定了性骚扰:“不受欢迎的性要求,不受欢迎的性接触,不受欢迎的品头、非品头或身体上涉及性的行径;涉及性的行径,借此营造在性方面有敌意或具威胁性的环境。”(李慧英,2002:170) 二,扩展性别暴力内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我们已经看到,针对家庭暴力、性暴力等性别暴力的定义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但是,在对性别暴力概念的使用上,仍然存在狭窄化的情况。目前中国国内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沿袭1993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的定义,将性别暴力等同于针对妇女的暴力。 在“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4000110391)的工作中,我们接触到非常多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许多种形式的性别暴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 如何定义性别暴力,对于预防和制止性别暴力的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性别暴力定义以偏盖全,或者遗漏了一些形式,那些被遗漏的性别暴力形式便无法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得到有力的干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形式暴力的蔓延。 毕竟,许多进行預防和制止性别暴力工作的专业人士,是依据针对性别暴力的定义来进行相关工作的,比如警察、司法系统依据性别暴力的定义提供干預,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系统同样根据这一定义来提供社会服务,政策制定系统根据定义来制定相关政策,传媒系统通过定义来进行宣传倡导,等等。 所以,在笔者看来,如果对性别暴力的定义不充分,就会纵容暴力;而只有尽可能囊括所有形式的性别暴力,才会真正对受暴人起到保护,对实暴者起到警戒和惩罚的作用。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限度地扩大“性别暴力”的内涵。 在笔者看来,只要是基于性别不平等、性别歧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暴力,均可以归入性别暴力。也就是说,性别暴力的概念,应该包括所有基于性别政治和性政治权力关系下的暴力。 事实上,“基于性别的暴力”这名词本身便包括了更广泛的一切与性别权利相关的领域的暴力。我们今天只不过是希望努力还原这个词汇本应该具有的内涵,这需要我们有更强的社会性别敏感,以及对暴力与社会性别机制关系的更深入认识。 国际社会对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充实性别暴力的定义是持接纳态度的。2006年,联合国第61届会议的秘书长报告《关于侵害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的深入研究》中便说到:在社会急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对心理、情感虐待和暴力表现出的不同形式、社会和文化规范对妇女的暴力以及随着技术的使用(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不断演变和新出现的暴力进行命名。”新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新的性别暴力形式,如色情短信、色情图片,等等。但这种定义的新命名,应该不止于此。 将性别暴力超出针对妇女暴力进行定义,完全不代表笔者想否定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重要性,我只是希望,同时也关注其它形式的性别暴力,从而使制止性别暴力运动能够得到深入的、全面的开展。事实上,“家庭暴力”如今更多被“伴侣暴力”这一词汇所取代,便是对最初的家庭暴力内涵的新扩展。 性别暴力定义的完善,目前正值其时。这是因为: 1,国际社会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与认识。妇女无疑是性别暴力最深刻的受暴者,如果在针对妇女的暴力尚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其它性别暴力的形式,有可能会转移焦点,甚至影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干預。但如今,我们对暴力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便更有可能促进制止针对妇女暴力的工作。 2,国际社会对于性别多样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体现着对于社会性别实践的操演,以及性别身份选择等所有相关方面。进步的学术界与公共社会对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样性有了更多共识,对于男性、女性之外的跨性别的平等存在有了更大的接纳。 3,国际社会针对不同暴力形式的伤害有了更清楚的理解。除肢体暴力外,特别是对精神暴力的讨论非常深入了。 三,性别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还原“性别暴力”本应该具有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着手: 1,家庭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在中国,2001年4月,“禁止家庭暴力”条款明确写入修正后的《婚姻法》,2005年8月,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这里将女性视为伴侣暴力的唯一受害者。 伴侣暴力的受暴人多是女性,但大量调查也显示,约有10%的男人成为的受暴人。考虑到男性更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配偶的暴力对待,也更不愿意求助,所以这一数字可能还被隐藏了。(方刚,2011)但即使只有10%,这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侵权。但是,家庭暴力的研究与行动中,几乎完全看不到针对受暴男人的研究,这是严重不足的。 伴侣暴力的体现形式:肢体暴力、言语及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这四种形式均可能是女性针对男性的。白丝带热线咨询中不乏这样的实例。 通常认为,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少,有观念上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女性无法接受打丈夫的念头,社会文化也不接受女性打男人,其次就是生理上的,女性比男人弱。但在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女人坦承,自己会使用推搡、抓挠、打耳光等方式对男性伴侣进行虐待,甚至有每星期打断一个塑料洗衣板的案例。有人认为,女性对伴侣施暴通常是自卫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白丝带热线的咨询中,许多来电女性承认,她们是暴力的发起者,男性伴侣只是忍让、逃避。 在精神暴力方面,白丝带热线同样有女性侮辱、谩骂丈夫,不让其睡觉等施虐方式。女性的“唠叨”是否会造成男性的极度恐惧或严重伤害?这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领域是有争议的。这种伤害往往被看轻,认为远不如男性加害人带给女性受暴人的恐惧与伤害,或者说,女性的“唠叨”本身是因为男性先对女性漠视才出现的。通常情况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不足以成为我们忽视此一种形式的伴侣暴力的借口。我们更不应该以后果是否严重来定义是否是暴力,而应该以是否侵犯人权来定义。 伴侣暴力中的性暴力,通常指“丈夫对妻子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行为)”。(孙秀艳,2012:71)不难发现,同样的情况妻子也可以对丈夫实施。白丝带热线的来电中,便有女性对丈夫的性能力进行羞辱性评价,从而构成精神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的一些男性来电者抱怨说,他们的伴侣只给他们非常少的零用钱。这不仅是对他们经济开支行为的控制,更威胁了他们的自尊,考虑到社会对男性经济支配能力的要求,来自伴侣的经济控制使他们在公共空间时常处于窘迫状态,威胁着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如何评价这种男性气质是一回事,经济控制对男性心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暴力中的姻亲冲突中,不能回避婆婆与儿媳之间的暴力关系,这可能是直接实施的,也可能是婆婆通过儿子对媳妇施暴。中国文化中的“孝”,使得一些丈夫在姻亲冲突中对妻子施暴。此时,受暴人虽然是女性,但加害者包括女性(婆婆)。婆媳冲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色彩,而婆婆对媳妇的指责,通常与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相关,所以,我们也视之为性别暴力。 此外,白丝带热线接到许多同性恋伴侣的来电,讨论他们之间的暴力问题。同志伴侣暴力,也应该属于家庭暴力关注的范畴。 2,性暴力受暴人与加害人内涵的扩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一书的定义,性暴力是指“在任何地点发生的由任何人强行施加的性行为、性行为企图、非意愿的性评论、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针对他人性特征的强迫行为(如心理恐吓、身体暴力或人身威胁),而不论该行为人与受暴人的关系如何,发生地点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和工作场所。”(转引自孙秀艳,2012:71) 请注意:这个定义中并没有专指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侵犯,也并没有说女性是性侵犯的唯一受害者。 (1)性骚扰与性侵犯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在当时曾引起争论,因为男性也可能是性骚扰的受暴人。 暴力的本质是权力关系,所以拥有权力的人对没有权力的人实施暴力。当女性拥有这样的权力时,也可以实施暴力。笔者此前曾发表关于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研究报告。(方刚,2012:200-209)虽然女性对男性的施暴在数量上比较少,但不等于不存在。我们定义和研究性别暴力的时候,必须有全面的视角。 事实是,性骚扰包括异性间的,也包括同性间的。其中异性间的性骚扰,不仅是男人针对女人的骚扰,也同样有女人对男人的骚扰,还有男人或女人对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的性骚扰。而同性间的性骚扰,既存在于男人之间,也存在于女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于跨性别者、生理间性人内部。这些性骚扰行为,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本质上都是性别歧视的。 近年有媒体曝光,原配妻子对丈夫的情人施暴。包括一位妻子纠结四名女性友人,当街将“小三”的衣服扒光被泼粪。这种当众扒衣的行为,明显属于女性针对女性的性侵害。虽然可能有人说,是那位没有在场的丈夫先婚姻出轨在先,妻子施暴在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妻子行为的性质。而类似的开脱之辞本身,是需要警惕的。 (2)强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将强奸界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行为。从共犯的视角看,丈夫之外的男子和妇女也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甚至,可以成为强奸的主体。帮助丈夫强奸其他女性的妻子,就是强奸的共犯。 虽然提到共同犯罪的情况,但以上刑法条文中,女性加害人,特别是男性受暴人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涉及。事实是,女性也可以成为强奸的唯一实施者,无论强奸男性,还是强奸女性。强奸的定义中,应该加入男对男、女对女、女对男这些不同形式的强奸。对这些强奸形式的忽视背后,是对“阴茎插入阴道”这一性交形式的“唯一正统地位”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强奸必须是“一般意义上的性行为,即男女生殖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丈夫强制妻子肛交、口交或者其他方式的性交合,不构成婚内强奸意义上的强制性行为,而应当以强制猥亵罪或侮辱妇女罪论处。”(冀祥德,2012:59)这些论点,更是对“性”这一概念的理解缺乏现代视角。性不只是阴茎插入阴道的活塞运动,而是一个全面的,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强奸显然不应该仅限于阴茎与阴道的关系。 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的定义只是针对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具有父权思想的。男人强奸男人,也被中国刑法关注到了。但是,女人强奸女人,被彻底地忽视,而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对性别暴力内涵进行扩展时,笔者希望强调:强奸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强奸,还包括女人对男人的强奸,同性别间的强奸,对跨性别者及生理间性人的强奸。而且,这些都是基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的,针对性别的暴力。 3,其它暴力形式受暴人内涵的扩展 (1)美貌暴力。这原本指针对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女性的歧视性暴力。以往在谈论美貌暴力时,均强调针对女性的美貌暴力、苗条暴力,但事实是,对不符合传统“男性美”的男性的歧视同样存在。他们可能不被指责为“不够美丽”,但可能因为“不够高大”或“太丑”而受到歧视。 (2)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一直被认为是性别暴力的内涵之一,事实是,针对男孩子的拐卖更为常见,而这同样是针对性别的,因为男性更被“看重”,更“值钱”
参考文献:(从略)